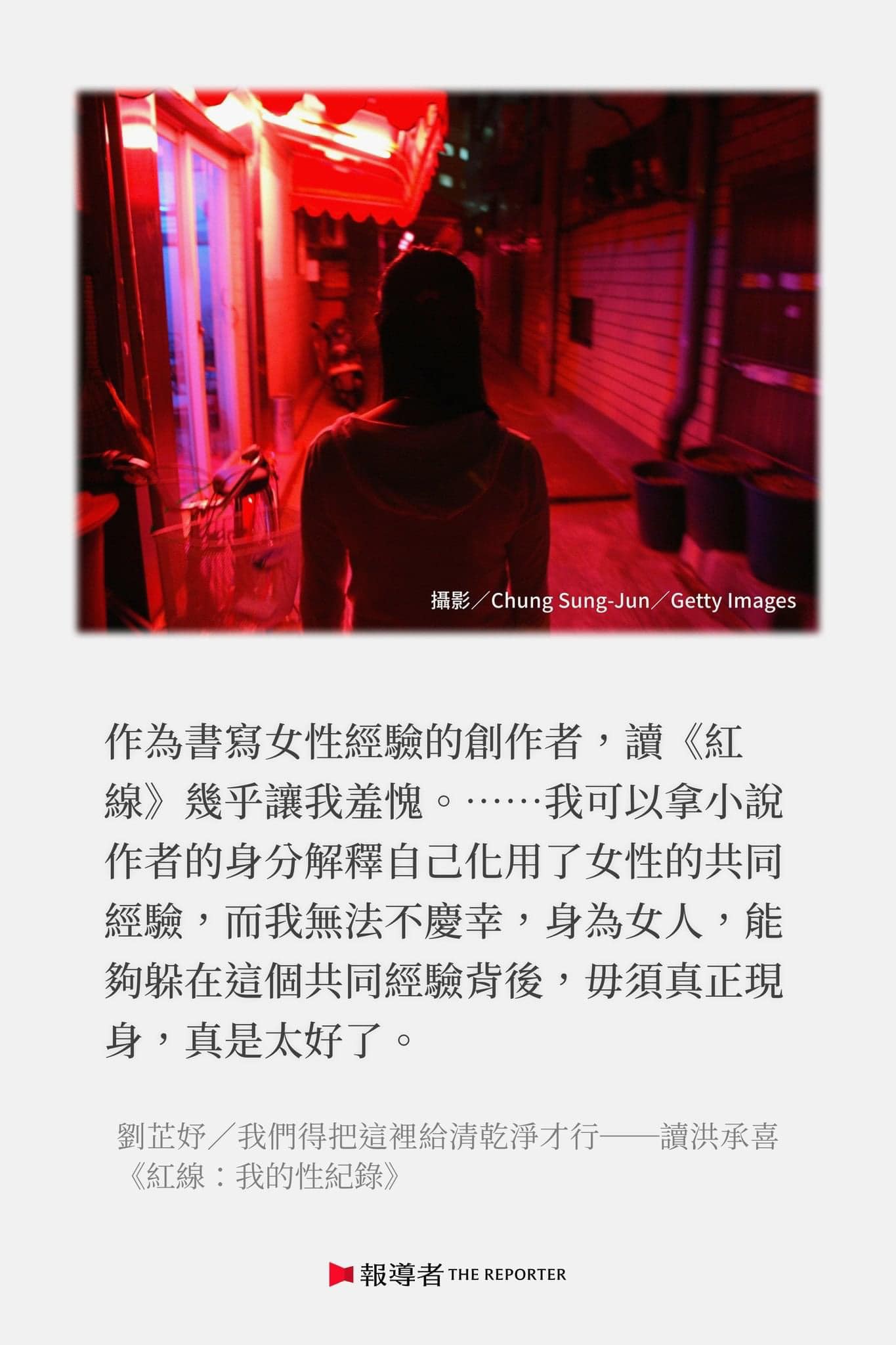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──讀洪承喜《紅線:我的性紀錄》
從《紅線:我的性紀錄》這個直白的書名,我們可以窺見此書內容約莫是忠實描述作者自己的性經驗,這可能會讓許多人輕易認定這本書就只是這樣而已,反正,一位女性只要願意寫出她的性經驗與性創傷,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聲嘶力竭地血淚控訴,就算得上是平權大躍進了,是吧?
事實雖是如此,但卻不只如此:誠實寫下自己的性經驗,無論對台灣或韓國的女性而言,絕對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;但這本書的珍貴之處,並不僅僅在於誠實,而是作者從自身性經驗之中,像是刺入了探針那樣地,沿著自己的性器與他人插入的性器之交合處,勾勒出女性必須承接的那些無以名狀之物。洪承喜所逐筆描摹的,並非僅是性愛、強姦、騷擾、自慰、懷孕、性交易、性剝削,以至於人工流產⋯⋯這些用簡單名詞就能想像出的女性身體經驗,更有隱藏在這些與性相關的經驗背後,之所以導致社會傾斜的「越想越不對勁」。
《紅線》作為一本「害蟲圖鑑」
雖然在台灣目前的社群網路中,「越想越不對勁」這個說法充滿了負面的嘲弄意涵,然而這卻是任何社會在所有議題上,想要取得進步的開端:質疑我們身處環境中所有的理所當然,讓那些「一直都是這樣」、「本來就該這樣」、「質疑這種事的人才有問題」,以至於無人能夠輕易挑戰的傳統、慣習,甚至文化,得以被攤在陽光下檢視,才有可能避免這些「理所當然」成為罪惡與傷害的溫床。
每一種渴望改變世界的倡議行動,必定會遇到的第一個關卡都是「描述問題」——倡議者需要描摹問題情境,甚至為之命名,讓其他人了解自己的訴求。當然,每種倡議一開始都必然會遇到許多保守派,他們可能是既得利益者,可能身為被壓迫者但囿於結構盲點而不自知,也或許是純粹無法理解問題何在,認為沒有必要作出改變,都是這些人沒事找碴。但漸漸地,藉由不同的敘述者現身說法,會有更多人願意理解這個被描述與命名的問題情境;甚至連非當事者,也可能基於同理或同情而加入支持的行列。
於是,在「越想越不對勁」之後,我們應當盡可能刻畫出那些不對勁的輪廓,熟悉它們的原生地、出沒時機、喜好情境,甚至是常見的群聚共生類型,將它們依照界門綱目科屬種那樣嘗試定義並命名,說出來、寫下來、甚至展演出來。唯有一再從日常中提取出這些「不對勁」,讓它們失去「本應如此」的保護色而顯得荒誕,才能像是找出害蟲那樣,使其易於辨識並剔除。
依照這樣的邏輯說來,《紅線:我的性紀錄》幾乎可說是一本害蟲圖鑑。
台灣比韓國還要性別平等?
在過往的閱讀視聽經驗中,我一直認為自己生長在一個相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,「雖然還不夠但確實更接近性別平等」的國度,尤其在閱讀近年韓國興起的女性經驗書寫時,我常覺得韓國女性現今所煩惱的那一種不平等,似乎比較接近台灣十幾二十年前的社會氛圍。我曾經以為,韓國如今所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已經描摹、命名過的那些;我以為我們在台灣理當處理更深層也更難以對付的歧見,那些歧見之所以難以對付,是因為我們無法使用既有的定義來描述這些「不對勁」,必須重新勾勒,才能讓它們展現在世人眼前。
然而在讀完《紅線》之後,我開始懷疑這樣的「自以為進步」,說不定並非全然事實。因為,洪承喜在《紅線》一書中所描寫的那些不對勁,絲毫不像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台灣,而是現時、此刻,我們自己。
洪承喜藉由自己的親身經歷,甚至是從那些會被說成「破麻活該」的經驗中,像是拔起一株因為長期置之不理而早已盤根錯節的巨木那般,徒手深入那些多數人都嫌骯髒汙穢的暗處,剝解出兩性關係之所以歪斜的龐然根系。有無數蟲鳥藤蔓攀附著這根巨木,會群起攻擊企圖改變現狀的人;其下的根系也不只是緊抓著泥土,更可能深入地底,與其他同樣巨大的議題相互糾纏。而有鑒於人類歷史上數千年以來對性的諱言避談,每一次往下掏挖,都可能掘出糞尿蟲卵腐屍混雜、令人光看一眼就想吐的穢物。
而寫下這樣一本書的人,尤其是女人,並非以光鮮亮麗性感優雅等姿態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女人,在用雙手掘出這些泥土以及更多腐臭的過程中,她必定滿身汙穢,並且不可避免地被他人當成汙穢本身,而非為了改變世界扭轉不公而弄得自己一身髒汙的英雄。
要想擺脫污名,必得先承受污名
我曾深信,韓國目前在處理的性別不平等,是表土上的紛雜與歪曲,而台灣的我們,已經開始處理埋藏得更深的議題;然而洪承喜在這種禁忌議題上自我揭露的極限尺度,卻開了我的眼界。我是一位寫作者,也是一名女性,但我不僅無法用這種幾乎是紀錄片形式的文體來記錄我的性經驗,當我把自己的經驗轉化到虛構小說中時,我甚至還費盡心思將故事情節及人物設定推離自身,在寫下身為女性的萬般艱難的同時,盡最大的可能,遠離那些萬般艱難。
甚至可以說,出現在我小說裡的每一個字與每一個角色,都在嘶聲吶喊著:「不,我不是作者,我不是她!」
但真的是這樣嗎?
或者說,有可能是這樣嗎?
作為一位書寫女性經驗的創作者,讀《紅線:我的性紀錄》幾乎讓我羞愧。我為什麼這麼害怕與性扯上關係?我為什麼想要假裝我筆下的眼淚,只是故事裡那個倒霉鬼的痛楚與傷痕?我可以拿小說作者這個身分解釋自己化用了女性的共同經驗,而我無法不慶幸,身為女人,能夠躲在這個共同經驗背後,毋須真正現身,真是太好了。
我當然知道,「誠實面對自己與世界,才是和解與改變的第一步。」這種心靈雞湯,我看了二、三十年,從書籤小語、紙本雜誌、談話節目到IG上的手寫金句,閱聽媒材不知道都更新了幾輪,同樣的句型依然鋪天蓋地,幾乎成為基本款的普世真理。但論及真正的性,那就是個黑洞,在那裡,只有禁忌而沒有真理,比起知道「該做什麼」,更重要的恐怕是「不該做什麼」。
那些不該做的,洪承喜都做了,而其中最不該做的,就是把她所做的一切該與不該,都說出來。有多熟悉那些金句,就該有多清楚,在真實的世界裡,人們會怎麼看待像是洪承喜那樣,誠實到這個地步的「那種女人」。那些原該暖心的雞湯金句,到那個時候就會活生生血淋淋燒燙燙地澆在女人頭上,他們會說:「雖然說要誠實,但妳多少也該評估一下情況吧?」
這難道不是一種弔詭的悖論:希望擺脫污名,必得先承受污名。
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
洪承喜無視這些在台灣已經夠可怕、在韓國肯定更為巨大的潛規則,她傷痕累累地現身人前,寫下所有好與不好的性經驗,不僅揭露特定男性或社會氛圍對她個人的踐踏,更寫出在某些進步價值觀下被迫犧牲的女性感知,彷彿為了成就更龐大的男性理想,女性主義只是可適時拋捨的一環。她寫下他人對自己的傷害,更寫下自己曾經因為無知或因為方便而服膺這些價值觀的深刻反省。她的直言不諱,可不是那種自承性子直不會講話的卸責說詞,而是直指核心的真言,指認出那些眾人早已心知肚明卻難以改變的積惡。而從她毫不矯飾的和盤托出中,我們得以接近,並逐步包圍那些尚且難以描摹言說的黑暗物事。
讀完《紅線》,我彷彿看見一位全身髒臭到認不出原本是個人的女性,從冒著髒水的地底窟窿裡爬出來,站在我面前,笑著說:「看到了嗎?那底下,是長這個樣子的,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。」
我突然醒悟,到頭來,如果我們無法真正處理「性」,如果我們無法面對那個在人類文化中,始終躲藏在晦暗汙濁的地底深處的濕黏怪物,無法忍著惡臭與噁心,將之洗乾淨、還原出應有的人形,而只是在外圍,乾乾淨淨地調整制度表象,或者纖塵不染地說幾句臭酸雞湯,就想藉此獲得真實的平等,那就是,癡人說夢而已。
如果只有一個甘冒罵名的洪承喜,而沒有更多人願意直面「性」的扭曲與荒謬,那麼平等的可能也將繼續與其一同埋藏在深不可及的地底,發臭腐爛。
我們得把這裡給清乾淨才行。
**本文原刊登於《報導者》,圖片亦採用報導者於臉書刊登之圖片。